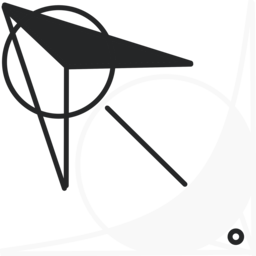转载:写作建议

存档我觉得好的资料,包括文学审美和经济研究的建议。
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下,没人知道经济学将走向何方。有人说经济学是屠龙之术,可这世界毕竟无龙可屠;有人说经济学过度数学化,早已远离世界的真实;有人说经济学家是只会用假设来解决方法…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研究范式交错纵横,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在今天,经济学越来越像建构主义的寓言题材,用数据和例子讲好一个我们需要的寓言,从这一点看,经济和文学倒有了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在这里收集整理个人喜爱的文章,以作参考。
文学
毛姆的「写作建议」
1、你必须比观众先感到厌倦。
2、写作者的座右铭必须是:能删则删,删了再删,直达观众注意力的顶点。
3、我们作家必须研究的还是普通人。普通人才是作家更为肥沃的土壤。
4、他喜欢使用更强有力的词甚于那些悦耳的。
5、数年后我才明白,写作是一门精巧的艺术,要经过辛苦努力才能获得。
6、努力做自己没有天赋的事是无用的。
7、我为自己词汇的贫乏感到吃惊,于是带着纸笔去大英博物馆,记下奇珍异宝的名字、古旧珐琅的拜占庭式颜色、织物给肉体带来的感受,然后精心构想一些句子把这些都放进去。我很幸运,没找到什么机会用这些材料;它们还躺在那本旧笔记本中,为想写废话的人预备着。
8、我想摒弃浮华辞藻,用尽量直白、不矫饰的方式写作。
9、我发现了自己的局限,于我而言,唯一的明智之举就是将目标设定在这个局限之内自己所能达到的最优秀境地。我知道自己没什么抒情的特质。
10、我琢磨着,自己似乎应该将目标定在清晰、简洁和悦耳上。
11、在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两种类型的晦涩,一种乃是源于疏忽,另一种则是有意为之。人们写得晦涩,经常是因为他们没有不辞辛苦地学习怎样写得明白。造成晦涩的另一个起因,是作者自己对自己的意思都不十分确定。
12、很多作家不是写作前,而是在写作时才展开思考,也就是笔杆促生了思想。这也确实是作家必须时常提防的危险。
13、人们很容易说服自己,认为某个他不怎么明白的词语包含着远多于他所意识到的意思。
14、要达到清晰,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15、简洁和自然才是“卓越”最真实的标志。
16、悦耳是我提及的三种特征中的最后一个,相当多的读者以及很多令人尊崇的作家都缺乏这一品质。
17、语词有分量、有声响、有外表,只有考虑到这些,你才能写出优美动听的句子。
18、我不照自己的愿望写作,我照自己的能力写作。
19、牵强的、陈旧的,甚至做作的词,只要比直爽的、明确的词好听,或者赋予句子更好的平衡感,我就不会认为它不合适。尽管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动听的声音妥协,却不应该对使意思模糊的词让步。
20、我想作者最好就是具有比读者更强的厌倦机能,这样就能在读者之前体察到厌倦了。
21、人们一旦努力形成一种文风,其后就很少能够完全自由地写作了。
22、如果你能写得明晰、简洁、悦耳并且生动,那么你将写得很完美,你将写得像伏尔泰一样。
23、好的文风没有努力过的痕迹,你所写的文字应该看起来像是妙手偶得。
24、如果我到底还是达到了从容的效果,那也只是通过艰苦的努力得来的。
25、人们应当用属于其所处时期的方式进行写作。语音是生动且变化着的;努力像身处遥远过去的作家们那样写作,只能导致不自然。
26、我情愿一个作家很世俗,也不希望他矫揉造作;因为生活就是世俗的,作家追求的就是生活。
27、在我看来,很多作家根本不观察生活,而只是从他们幻想的很多形象当中,依现有的样子创造出他们的人物来。他们就像是根据对古董的记忆绘出图案的绘图员,从来不试着去画活生生的模特。他们充其量也只能给心中的幻想以似是而非的形状而已。
28、知识分子愚蠢的偏见在于认为只有他们的知识才识起作用的。真、善、美并非那些上费用昂贵的学校、泡在图书馆或经常出入博物馆的人的特权。艺术家没有借口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艺术家如果以为自己的知识比别人的知识更重要,那他就是傻瓜;如果他不能移平等的立场愉快地面对别人,那他就是个笨蛋。
29、作家可以放心,他自己希望忘记的作品也是会被读者忘记的。
30、我把书籍放到一边,只是因为意识到时光流逝,而生活才是我的正事。
加缪 1957 年诺奖演讲《艺术家及其时代》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
秉承自由精神的贵学院慷慨授予我这份殊荣,我自认我的成就远远配不上它的分量,所以更是由衷地心怀感激。所有人都渴望得到认可,艺术家就更为如此。我也是一样。只有当我将你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与真实的我进行比较之后,我才真正理解你们何以作了这样一个决定。一个尚且年轻的人,除了疑惑一无所有,他的作品尚未成型,并且习惯于在工作中孤独地生活,对各种示好也退避三舍,对于这样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来说,突然被逮到,并抛置于这耀眼的聚光灯下,又怎么能不感到一种恐慌呢?当欧洲其他的作家,哪怕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些作家,都被迫保持沉默,当他的故土,正遭受着无止境的苦难,他将以怎样的心情来接受这份荣誉呢?
我就经历了这种内心的惶恐与不安。为了重新获得平静,我只能接受这份命运慷慨的馈赠。既然我的成就无法与这份奖项匹配,我便只能倚赖那份支撑着我人生的信念,即便在最艰难的境况下也未曾抛却我的那份信念:那就是我对我的艺术以及对作家这一角色的看法。让我怀着感激和友好的心情,对大家尽可能简短地表达一下这个想法。
于我而言,没有艺术,我便无法存活。但我从没有把这份艺术置于一切之上,相反,它之所以对我而言不可或缺,正是因为它与所有人紧紧相连,并且允许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和大家一样生活下去。艺术在我看来并不是一场孤独的狂欢。艺术是一种手段,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同的苦难与欢乐,从而感动了大多数的人。所以它迫使艺术家不再自我孤立,使其屈从于一种最为质朴、最为普世的真理。而通常情况下,那个自认与众不同而选择艺术生涯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只有承认自己与众生的共性,他的艺术和他的独特才能从中得到滋养。正是在这种自身与他者不断的往来中、在与他不可搁置的美以及不可抽离的群体的交往之中,艺术家得到了自我锤炼。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艺术家不会蔑视任何东西;他们要求自己必须理解一切,而不是评判一切。如果他们必须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一个阵营,那他们或许只能属于尼采的伟大言论中所构建的那种社会:一个由创造者而不是评判者来统治的社会,无论这里的创造者是劳动人民还是知识分子。
同样地,作家这一角色也被赋予了艰难的职责。身为作家,在如今这个年代,他不该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他应该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被孤立,也将失去他的艺术。一个作家,若是与暴君为伍,那么即便暴君有千军万马与之同行,他也依然无法摆脱那种孤独。但世界另一头,一个被遗弃在屈辱中的无名之囚,他的沉默却足以一次又一次将作家从这种孤独的流放中拯救出来,只要他在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始终不忘这种沉默,并以艺术的方式来使这种沉默发出声响。
我们中任何人都没有伟大到足以承担这一使命。但是在他一生的境遇中,无论是门庭冷落还是扬名一时,无论是被压制于暴政的桎梏之下还是拥有一时的言论自由,作家只有忠心耿耿竭尽所能地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他的职业才能因此变得伟大,他才能得到民众发自肺腑的正名。作家的使命,就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这个使命不应屈服于谎言和奴役,因为在谎言和奴役统治的土地上,处处囚禁着孤独的灵魂。无论我们作为个人有着怎样的弱点,我们职业的高贵却永远扎根在两个并不容易坚守的承诺里:对于知晓的事,绝无谎言;对于任何压迫,反抗到底。
在二十多年的荒诞历程中,孤立无援的我和同代人一样,迷失在时代的跌宕变迁中,仅靠内心隐隐的一种感觉支撑着:在当今这个世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这一行为肩负使命,并迫使你不仅仅去写作。它尤其迫使我按我自己的方式,以我的一己之力,与所有和我一样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一起去承担起我们共有的那种痛苦与希冀。这些人,出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希特勒政权建立和最初的革命浪潮掀起时,他们又正值二十多岁。接着,像是要使他们的经历更加完整,他们又经历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经历了那个满目疮痍、遍地集中营和牢狱的欧洲,而如今,正是他们这些人,又要在毁灭性核武器的威胁下,抚育他们的下一代,完成他们的使命。我想,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主张,在与他们不断斗争的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只是因为与日俱增的绝望,而做出了耻辱之举,并且堕入了这个时代所盛行的虚无主义。但是,不论是在我们国家,还是在整个欧洲,我们中的大多数,仍然拒绝虚无主义,仍在寻找一种正义。我们需要锻造一种在多事之秋生活的艺术,为的是能够涅槃重生,然后坦然地与那历史进程中的死亡本能作斗争。
或许,每代人都自信肩负着重塑世界的使命。然而,我们这代人却知道,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或许更伟大,因为我们的使命是:不让这个世界分崩离析。我们继承的,是一段残破的历史,它混杂着革命的失败、走火入魔的科技、已经死去的诸神和穷途末路的意识形态,纵使在这样的时代,任何平庸的势力都能让这个世界毁于一旦,但这种平庸的势力只有否定的力量,在理智自甘堕落成仇恨与压迫的奴隶时,这种否定的力量并不能教会我们这代人在内心和外部世界重新修建起一点点能够给予生命和死亡以尊严的东西。在这样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崩塌的世界面前,我们伟大的裁判官们建立的恐怕永远是死亡的国度,而我们这代人知道,我们应该在与时间疯狂赛跑的同时,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一种不屈从于任何奴役的和平,重新调和工作与文化的关系,并与全世界所有人携起手来,构建一种联盟。没有人能够确定我们这代人是否能完成这项浩大的任务,但是,我们确定的是,他们已经遍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时刻准备着为之赴死,无怨无悔。正是这些人,值得我们尊敬和鼓励,无论在何时何地——尤其是在他们牺牲的地方。总之,我想把你们刚刚授予我的荣耀转献给他们,相信你们也会感同身受。
与此同时,在说了作家职业的高尚之后,我想要还原作家的真实模样,除了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共享的身份之外,他没有其他身份。他既脆弱又固执;他无法永远保持公正,却又热切追寻着公正;在所有人的视线中,他默默构建着自己的作品,既不以之为耻,也不引以为傲,他永无止息地在痛苦与美好中被撕扯,最终是为了从他这双重的存在中,提炼出他固执地想要在历史的废墟中创建起来的东西。这么说完,谁还能期待他给出现成的答案和完美的道德信条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捕捉的,总是有待征服的。自由固然是令人振奋的,但实践起来也同样是危险的、艰难的。我们必须走向这两个目标,艰苦卓绝、征途漫漫,却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由此,哪个有着自知之明的作家还敢自诩为美德的传道者?至于我,我必须再说一次,这完全不是我的身份。我从来未能放弃生命中的光和幸福,不能放弃自由的生活,这些东西自小就伴随着我成长。这种怀旧之情虽然也让我犯了不少错误,却无疑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职业,帮助我毫不犹豫地站在那些沉默的人身边,那些人,除了从回忆中追索那一点点短暂而自由的幸福,在这个世上便无以为继。
现在,我向大家还原了真实的我,你们知道了我的浅薄有限,知道了我得益于他人,也知道了我艰难的信仰,作为结束,我终于能更自如地表达诸位授予我这份荣誉的广博与慷慨,也能更自如地对你们说,我接受这份荣誉,并要把它视作为一种致敬,向所有和我一样经历了战斗,却没有获得任何殊荣,只是饱经了苦难与迫害的人致敬。最后,我要发自肺腑地对诸位表示感谢,并公开地,以感恩的心,向你们作出一个古老的承诺,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每天都会在静默中向自己作出的古老的承诺,那便是——忠诚。
恰克(《搏击俱乐部》作者)的写作指南
再过六秒钟,你会恨死我。 但再过六个月,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
从现在开始——至少接下来半年之内——你不能用“想”动词。这包括:觉得,知道,明白,懂得,相信,想要,记得,想象,欲求,还有其他那一百个你喜欢用的词。
这张单子还包括:爱和恨。 它也包括:是和有,但这两个过一阵再说。
直到圣诞节左右,你都不能写:肯尼觉得莫妮卡也许不喜欢他夜里外出…… 作为代替,你必须把这句话分解成:“有些早晨,肯尼在外面待得很晚,错过最后一班公交,直到他不得不搭便车或付钱搭出租,然后回到家发现莫妮卡在装睡,因为她从不如此安静地睡着,那些早晨,她只会把自己那杯咖啡放进微波炉里。从没有他的。”
比起写你的角色知道什么,你现在必须提供细节,让读者知道那些事。 比起写一个角色想要什么东西,你现在必须描述那个东西,让读者也想要它。 比起说:“亚当知道格温喜欢他。”你必须要说:“在课间,他去打开他的储物柜时,格温总是倚在它上面。她会翻翻眼睛,用一只脚把自己推开,在被漆过的金属上留下一道黑色的鞋跟印,但她也留下了她的香水味。组合锁上还有她臀部的温度。下一个课间,格温又会倚在那儿。”
简单来说,没有捷径了。只有具体的感官细节:动作,气味,味道,声音,以及感觉。 一般情况下,作者总会在一段话的开头使用这些“想”动词(在这里,你可以管他们叫“中心句”,我等会儿在抱怨这个)。某种意义上,他们点出了整段话的意图。接下来的部分来详细解释这些意图。
比如说:“布兰达知道她不可能赶得上截止时间。她从桥那边过来,经过八或九个出口。她的手机没电了。家里,狗需要出去散步,要不就会弄得一团乱需要收拾。再加上她答应要帮邻居浇花……”
你看出开场的中心句如何抢了下面那段话的风头吗?别这么干。 最少也要把开场白拿掉,放在其他所有句子的后面。更好的是,把他换个地方,改成:布兰达赶不上截止时间了。
思考是抽象的。了解和相信是无形的。如果你只展现出物理活动和角色的细节,让你的读者去执行思考和了解,以及爱与恨的话,你的故事总会更有力。
别告诉你的读者“丽莎恨汤姆。”作为代替,想法庭上的律师一样据理力争,用细节说话,展示出每一件证据。
比如说:“点名时,在老师叫到汤姆的名字之后的一喘气之间,在他应答之前的那个瞬间,就在那时,丽莎会小声叫出‘讨厌鬼’。就在汤姆说‘到’的时候”。
新手作者最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让他们的角色一个人待着。写作时,你可以是一个人。阅读时,你的读者可以是一个人。但你的角色应该很少、很少一个人待着。因为一个孤独的角色会开始思考、担忧、或者好奇。 比如说:“在等公交时,马克开始担心这趟路程会花费多久……”
更好的展示方法可以是:“时刻表写着公交会在中午到达,但马克的表显示已经 11:57 了。你可以看到路的尽头,一直到购物中心的那本,一辆巴士都没有。毫无疑问,司机停在了中转站,路线的最那头,正在打盹。司机很发送,睡得正香,而马克就要迟到了。或者更早,司机正在喝酒,那他就会停在路边,收马克 75 分钱来给他一场严重交通事故中的凄惨死亡……”
一个独自一人的角色必须进入幻想或回忆中,但即便那样你也不能用“想”动词,或者任何它的抽象动词亲戚们。 哦,你可以忘掉“忘记”和“记得”这两个词了。 再不能用这种转换句:“旺达记得尼尔森以前如何梳过她的头发。” 再说一遍,分解。别走捷径。
更好的是,让你的角色遇到另一个角色。越快越好。 让他们待在一起,开始活动。让他们的活动和谈话展现出他们的想法。你一一别进到他们的脑袋里面去。
在你躲避“想”动词时,要特别注意“是”和“有”这两个平凡的动词。 比如说:“安的眼睛是蓝色的。” “安有蓝色的眼睛。”要换成: “安咳了一声,抬起手在面前挥舞,把香烟烟雾从她的眼睛,蓝色的眼睛,中赶走,然后微笑道……”
比起使用平淡的“是”和“有”陈述句,试着把一个角色是什么和有什么的细节埋进动作或者手势里。最基础地,这就是呈现而非讲述你的故事。 很久以后,一旦你学会了分解你的角色,你就会恨死那些偷懒的作者,他们只满足于:“吉姆坐在电话旁边,想知道为什么阿曼达没有打来。”
拜托,此时此刻,随便你怎么恨我,但别用“想”动词。等到圣诞节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吧,但我打赌你不会的。
……这个月的作业是,读一遍你的作品,圈出每一个“想”动词来。然后,找到消灭他们的办法。通过分解它来消灭它。 然后,读一些已出版的小说,做相同的事。不要手下留情。
“马蒂想象着鱼儿们,在月光下跳动……” “南希回忆着那酒的味道……” “拉里知道他死定了……”
找到它们,在那之后,找到重写他们的方式,让他们变得更有力。
经济学
选题建议
——上海金融学院何晓波
How to get started on research in economics?
—— Steve Pischke(2009)
也可以在这里看:Resources for Economics PhD Students
萨缪尔森 | 为什么写《经济学》的那个人是我?
来源: 经济学江湖事
本文为萨缪尔森为《经济学》出版五十周年而作,来自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Samuelson No. 587。译者:吕吉尔 ,赖建诚老师转发。王老虎修改了部分文字,希望没有违拗译者的原意。因为喜欢这篇文章而分享于此,添加原创保护标志的原因是保护吕老师的译者权利,吕老师请朋友们多多指正,以便完善译稿。对于您的指正,译者表示由衷的感谢!译者邮箱: zjjier@163.com
《经济学》五十华诞
《经济学》迎来了第五十个生日,在这半个世纪里,它见证了经济学的长足发展。经济学已经走过了慢慢长路,到现今仍无资格吹嘘自己已臻于严密科学之境,任何社会科学恐怕都是如此。经济学永远是融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学科,充满活力的经济学与迂腐陈旧的经济学之间存在天壤之别。
今天,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与日俱增,不论在政府部门、私营部门,还是在学术界,统计数据库的数据量相比于 1940 年代末出现爆炸性增长。现在,计算机可以光速获得和处理统计信息和各种知识,而我们可以迅捷地获得信息。不论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受益于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进步,其受益程度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部门。
尽管如此,经济学基础领域却裹足不前。世人已经从历史(至少是经济历史)中学到了一些经济原理,并加以刻苦研究和检验。经济学家将反复无常的经济不景气和引起虚假繁荣的通货膨胀当做实验小白鼠,像化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进行受控实验。(译者在此省略一句话。)与此同时,完全自由竞争市场却未能给人类带来机会平等和收入平等。
“贫困始终与我们同在”这一事实迫使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演化为“混合经济”,既非自由放任的市场,也非罗宾汉的乌托邦。只有学习过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大众才能理解并确信,如何在自利驱动的个人进取与政府调控、维持稳定和再分配之间拿捏好中庸之道。无论是否情愿,混合经济必定是“有限的混合经济”。
回首往事
五十岁生日是回顾过去的绝佳时机。从这本独占鳌头的畅销教科书风行历史中,究竟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部教科书是如何诞生的呢?这得把目光拉回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和日本战败而告终,返回家园的人们让美国的大学人满为患。此时,恰逢经济学正步入一个黄金时代。1929 年到 1935 年的经济大萧条让经济学调转船头,摒弃曾经占据正统地位的老旧观念,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英国和美国采用了新方式动员本国经济为战争服务,这让 Hitler、Mussolini、Hirohito 连做梦都想不到。那时候,我们还不可能知道后来的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但它即将为战后数十年的经济增长搭建舞台。
学生们应该了解这一切。然而,我们这一辈教师们都知道,当时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内容已经严重过时,这点令人十分痛心。这也难怪初学者对经济学普遍感觉厌倦。我在哈佛和 MIT 上课时,常常看到学生们目光呆滞的表情。
当《经济学》终于在 1948 年面世时,“宏观经济学”—研究决社会就业的因素、价格水平和通胀率、实际 GNP 增长等问题–这个词尚未收入词典。那时,即便是我没有把大炮和黄油写进微观经济学中,也一定会有人那么做。是时候让经济学入门课程脱胎换骨了。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个人是我?
那时,我刚刚从 MIT 辐射实验室回归经济系。我在辐射实验室为设计躲避地方轰炸机的自动伺服装置进行数学方面的研究,而我“渴望”回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来。那年我刚好 30 岁,正是而立之年,是编写教科书和创新论文的好时候。无独有偶,我的先期著作《经济分析基础》已经付梓,这本书让我在 25 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那时候,有前途的学者基本不写教科书,至少肯定不写大一、大二学生使用的基础教材,只有捉刀人才会做这件事。但是考虑到我已经发表了那么多研究论文,我的名气和获得终身任期的前景也让我可以游刃有余,于是我积极响应了 MIT 系主任邀我写一部新教科书的请求。由于太过自信,甚至是有些自以为是,我需要做的仅仅是满足我自己。我想,是时候召集一批经济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回到普通教育的战壕中来了。
精雕细琢
开始一项工程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要圆满完成它却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每当一章写就,油印机就嘎吱嘎吱地将它印出来,给我们 MIT 的学生试用。这种做法对我和教材的要求都很高,但我却乐在其中。我天真地预测一年就可以完成这项工作,谁知道居然写了三年。所有周末和暑假都被我奉献给了这份工作,努力将复杂的基本原理简化为简明易懂的教学内容,我的网球爱好不得不放弃了。我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想让“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变得生动活泼、激动人心的话,连最传统的经济学图表都要重新设计。
关键时刻
1948 年秋天,《经济学》第一版终于从印刷机上滚滚而出。无论前期工作有多艰辛,或梦想有多乐观,谁也无法确信未来结果将会是什么。幸运的是,这一处理经济学的新方法似乎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不论规模大小,很多大学都选择了这部新书,并且每次重印售馨之后,《经济学》又会让印刷机重新运转起来。
古根海姆学者奖把我带到了欧洲,在几座主要的城市里,我走访了市里的每家大书店,看是否能买到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的版本。除了想满足作者与生俱来的虚荣心以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还高兴地看到德国公民正经受最新主流经济学的抉择考验。
对该书的评论让这本书的热度急速升温。首先出手的是 John Kerrneth Galbraith,然后是保守派商业期刊《财富》的编辑。他预言下一代人都将学习 Samuelson 的《经济学》。虽然赞扬之声令人陶醉,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该书的经久不衰确实令我深感惊讶。其实 Galbraith 比我更有先见,《经济学》的确树立了一种新的、持久的范式。
一路坎坷
写书并不是只带给我乐趣。在参议员 Joseph McCarthy 强烈反对的日子里,当激进主义的指责从讲坛和教室里猛烈迸发时,我的书也遭到非难。一位保守的 MIT 男同学警告大学校长 Karl Compton 说,如果允许 PaulSamuelson 发表对“混合经济学”的辩解,他的学术声誉将受到危害。Compton 博士回应说,他的教员受制于审查制度的日子就是他辞去校长职务的日子。这在四十年后看来似乎有点儿滑稽可笑,但在那个能给教科书被扣上颠覆帽子的时代,任公立大学的教师决不是闹着玩的。(有一部优秀的教科书,先于我的教科书一年出版,一开始就被莫须有地恶意指控为马克思主义而被扼杀在萌芽中。)实际上,当你被右派掌掴时,其疼痛或许可以被来自左派的耳光部分抵消。1960 年代,学生行动主义在国内外校园里正热火朝天,两卷本《反萨缪尔森》应时出版,该书指控市场是狗咬狗自相残杀的场所,而我则是市场的坚定拥趸者,是自由放任世界的辩护者和资本主义的忠实走狗。
每一阵寒风都给人带来有益的教训,因此,每当涉及到有争议的事情,我就特别小心地写作。当然并不是说我在各方面都完美无缺。而是说,我只能通过尽量公平地陈述与主流经济学中流行见解对立的主张来实现。
面对主流经济学中各个流派的竞争,我始终准备充分且小心应对,这使《经济学》作为一部参考资料集的,始终立于潮流鳌头。甚至连苏维埃俄国也感到翻译此书的必要性,仅在一个月之内,全部译本就告售罄。(专家们告诉我,在斯大林时代,我的书被放在图书馆的特别预留书架上,与有关两性的书放在一起,除了获得特别许可的读者以外,一律禁止借阅。)在冷战后的时代,新的译本不仅在中国、日本、越南等四十多个国家得到授权,而且还在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得到授权。
永远年轻
如同一个孩子呈现出不同于父母个性的独特个性那样,《经济学》的情况如出一辙。起先,主动权在我手里;但后来,它凭自身实力反仆为主,我倒被它牵着鼻子走。随着岁月流逝,我的头发由金色变为褐色,然后变为灰色。但与永不变老的 Dorian Gray 肖像一样,《经济学》永远是 21 岁。它的封面从绿色改为蓝色,从棕色改为黑色;而现在又改为金色。在数百封师生来信和建议的帮助下,经济学在其封面里面进化、成熟。主流经济教义的历史学家们,像研究不同地层里骨骼和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们一样,可通过分析第一版如何被修改成第二版直至最终被修改成第十六版,来鉴定思想潮涨潮落的年代。
事情就是这样。这份工作充满艰辛,但非常值得。网球对我的召唤始终存在,无法抵挡其召唤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对 McGraw-Hill 说:“该付出的我已付出了。在我享受荣誉退休教授的美好生活时,让别人继续耕作我最感兴趣的研究之田吧。”McGraw-Hill 随口答道:“让我们为你找个合著者吧。我们将开列一份能力和看法你都赞赏、且与你趣味相投的经济学家名单。”因此,对完美 William Nordhaus 的寻找就这样开始了。
耶鲁离 MIT 只有 150 英里,就是在那儿,现实中的 Nordhaus 将被找到。唯一有帮助的是 Bill 已在 MIT 获得博士学位。自那以后,他在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任职,并先后被派驻(英国)剑桥、德里和维也纳,在此期间逐渐名声鹊起。正式证明,像 Gilbert 和 Sullivan 或 Rogers 和 Hart 一样,我们也是非常意气相投的一对。
如同经典童话故事一般,我们从此后就一直幸福地生活着。事关紧要的是,该书仍然年轻,指向经济学主流将要流去的方向。
科学?艺术?
为什么在大多数大学里经济学都成为人数最多的选修课?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学涉及到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当通货膨胀来临时,我们谁都逃不了。当经济衰退来袭时,浪潮波及每条船只。而早起找虫吃的鸟儿,需要了解供求关系。仅靠有限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和决心要改善和改革社会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说,也都需要这样。
良知经济学并非完全显而易见。你从家里随身带来大学的常识不会让你理解为什么富国和穷国能同时双双从自由国际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要是没有学过好的比较优势课程,那么你的参议员也不会理解这一点。)在另一方面,在你掌握了所谓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训导之后,就不会再有神秘可言了。如果它不营造良知,那么它就不是好经济学。
经济学的第一门课程不会让你成为大师,擅于理解和诠释错综复杂而深奥难解的话题。但基于各地学生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你的最佳经济学课程将是你的入门课程。在你步入了这一陌生而奇妙的思想花园之后,世界将永远不再是同一个世界了。而当你多年后回顾这段经历时,即使是当时你不甚理解的东西也将已经明显成熟。
尽情享受吧!
Paul A. Samuelson
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MIT
1998 年
陆铭:给搞实证研究学者的经验建议
“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是 2004 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这文章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出乎我的意料,也说明实证研究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个时候,的确需要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帮大家澄清一下对计量的一些认识。
今天,我特别想帮大家清除几个误解,这几个误解也恰恰是我在和同学接触的过程当中,从同学嘴里讲出来的误解,所以不是我生造出来的。
第一个误解是,实证研究就是应用性的,应用性的就不够学术,没什么价值,好像就是回答了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发现的结论好像是我们都知道的。
第二个就是大家都会经常讲的一句话,实证研究好做,比理论研究容易做,理论研究做不下去了就做实证研究。讲到这里,这个寒假刚刚迎来了我原来的一个学生,现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博士,她最近做的工作和 social economics 有关系,做的是理论。我们在寒假碰到的时候就谈,我就问她,为什么你这个课题不做实证呢?她说实证太难做了。所以我想,在某些问题上,不是像大家所想的,理论做不了就做实证,可能正好是反过来,是实证做不了去做理论。我等会儿还会讲实证和理论的关系,我会告诉大家,理论和实证都非常重要,而且是互补的。
第三,同学们常常认为实证研究很简单,只要把数据往电脑里一放,结果就出来了,就可以写文章了。有一次,一位同事不无自嘲的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觉得很心虚,因为数据不是自己收集的,我们用的很多大样本数据都是别人收集的,idea 也不算新,不是自己的,然后程序都是现成的,stata 都是编好的。之后我们就把不是自己收集的数据,也不算太新的 idea,往 stata 里一放,就出结果了,觉得很心虚。而我们的同学觉得经济学研究的高手应该是满纸数学符号加上自己编的程序,再画出非常 fancy 的图形,这就是水平高。
第四个误解是,很多同学认为现在我们研究中国问题,应该做理论,因为理论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对于初学者来讲,考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的时候,都是考的微观和宏观,然后一年级上课的时候上的大量都是微观和宏观的理论,所以你们就觉得那就是经济学的主流,只有做这个才上档次,哪怕做中国的研究,也应该把中国的问题写成数学,甚至干脆就不做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研究。那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就应该首先做理论呢?
今天接下来我要讲的这几个问题就想尝试着去清除在大家脑子里面的几个误解。我今天会讲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做实证研究?第二个就是,实证跟理论,包括思想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第三,实证研究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又怎样的关系?第四,如何完成一项实证研究?
一、为什么要做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和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我想有这么几个:
第一,实证研究是用来检验理论的。因为对经济学家来讲,我们有太多的理论,但是在现实中哪个理论正确与否,更重要或更不重要,其实离开了实践,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这是实证研究重要的第一个方面。而且从经济学的科学化的道路来讲,大家知道,第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发给计量经济学家的,最近这几年也是连着发给计量经济学家。大家知道,对于科学来讲,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它可以被证伪,那我们怎么知道理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经济学家实际上大量地依赖实证研究来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可以被证伪或者证实的科学。
第二,to challenge the theory(挑战理论)。当一个理论产生以后,大家知道特别是数学建模的理论,一旦数理逻辑建立起来,它就有自恰性和逻辑的科学性,因为它依赖于数学,数学的逻辑是严密的,所以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个理论会发现,当它得到的结论是 x 和 y 是正相关关系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这样的。那么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既有的理论没有正确地捕捉现实中的这个关系,或者说没有捕捉到 x 和 y 的关系中更重要的方面。那我们怎么知道呢?经济学就依赖实证的方法来看 x 和 y 到底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就说明既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正确的。在这个层面上,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就像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一样。
第三就是去发现一些净效应。我们知道,很多理论,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非常庞杂,关于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论。有的理论认为 x 和 y 正相关,有的理论认为它们负相关。大家知道,在做政策的时候就需要知道 x 和 y 到底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每一个机制在理论上单独来看可能都是对的,但对于制定政策的人来讲,如果不同的机制所预测的 x 和 y 的关系是相反的,那就需要知道,一旦这个政策下去,影响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理论是不能帮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不同的理论得到的方向完全可能是相反的,而且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想出不同的机制,使得在这个机制下两个变量正相关,在那个机制下负相关,
而且做理论的很多人往往喜欢标新立异,大家都认为 x 和 y 正相关,他就写一篇 paper 认为二者负相关,这是在国外发文章的捷径。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已经有非常多的理论经济学家在做这样的工作来揭示 x 和 y 的关系的不同机制。那我们在看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可能被这些理论搞糊涂了,它们到底哪个更重要?这个问题如果离开了计量经济学,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净效应到底是正是负?
第四个方面,我们再往前走一步,x 和 y 的关系,x 和 z 的关系,在理论上很清楚,但实证研究能告诉你哪个效应更强。大家知道在做政策的时候,比如有一笔 100 万的预算,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笔钱到底用来干哪件事情?比如,现在国外有个很著名的争论,就是教育的发展至少可以提出两个办法,第一是培训师资,第二就是缩小班级的规模,因为大家认为如果班级大了,每一个学生得到老师的关注就少了,这时候学生的成绩就会下降。那么对于政府来讲,就需要考虑,这 100 万到底去做哪件事情?且不说师资和学生之间的相关性,班级的规模和学生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是正是负,是否显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确定,就算是确定的,政府也需要知道应该把这笔钱花在缩小班级规模上还是提高师资水平上,做哪件事情更划算?
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在大样本的观察下,去做这件事情对学生成绩的提高程度有多大?对计量经济学家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准确地让计量的结果的系数要符合真实的效应的大小,这样就可以把一个计量分析里面的不同政策变量的效应去做比较,这就有利于政策效应的提高和资源配臵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改进人类的福利。而这个工作,是理论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事情,理论没有办法告诉我们这个效应到底有多大。
第五,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中,更为重要的是去 identify 这个机制,特别是在很多宏观的研究里面,我本人也做一些宏观的研究,比如做过不平等和增长的研究,有那么多的理论说这两者是负相关的,也有一些理论说是正相关的,我们现在的工作到了哪一步呢?实际上我们是看 net effect,在不同的理论机制下,我可以告诉你,二者总体上是负相关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难的工作就是,这个负相关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研究里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计量经济学很难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在理论上可能有好几个机制会告诉你这两者是负相关的,但到底是通过哪一个机制起作用的呢?这个机制的 identification 的重要性就在于,在做政策的时候,知道对什么样的机制去做政策?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收集数据的过程当中,很难区分出这样的机制。特别是在开始做计量还不是很有经验的时候,往往就想去看看 x 和 y 之间的关系。在做计量的时候,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只考虑 x 怎么度量,y 怎么度量,然后把这数据往机器里一放就可以了,但我们可能很少会去想,x 和 y 之间的中间变量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就会忽略掉这些东西,那最后就没有办法去看到底这些中间机制是什么了,这样就使得研究的档次上不去。而这些工作需要在做实证研究之前,对 x 到 y 的各种各样的机制要有一个全面而清楚的了解,并且在做问卷的时候就需要知道,怎么利用一些方法把各种机制独立开,必须要非常清楚地,让大家可以确信地认为你所看到的这个机制是非常干净的。“干净”这个词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它是指在我看到的 x 到 y 的关系里面,我可以让你确信,就是因为我说的这个机制,而不包含其他的东西,要达到这一点就有很多的方法。
第二个我要讲的问题是,我们处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时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经济学整个理论分析的架构已经基本上完善了,这意味着在经济学理论的进展上已经很难有重大突破,这就使得实证研究成为全世界研究的潮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这里要提到陈志俊,他是做产业组织理论的,学物理出身的。我想我刚才讲的这句话可能从我嘴里讲出来你们不太信,因为我现在很多工作是在做实证。他上学期来复旦,seminar 完了之后我们在一起吃饭时他就讲,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差不多了,所以大家现在就该用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有的时候我觉得数学太好是害人的”。这句话特别值得数学好的同学去琢磨。
第二点,在有一些研究领域里面,我们有太多的理论,但是经验的证据不足,而这些研究领域里面,现在前沿的领域往往由实证研究所推动。那么有一些什么样的领域呢?我等会儿还会反复再讲到这几个,第一个比如说 IO, 经验的 IO 现在成为了 IO 研究的前沿领域。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就是 personnel economics, 人事管理经济学,现在也是经验的研究非常热。
第三个方面就是,应用的微观和政策的评估。现在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政府的公共部门都非常庞大,而且如果看政府的公共开支在 GDP 中的比重,它在发达国家中是上升的,那么大量的公共开支到哪些地方去了呢?到 labor market, health, education 这几个领域里,在这些领域就碰到我刚讲的问题,一个政策下去到底有没有效果?哪个政策效果更大?政府也希望了解这个。比如我刚讲到小班的例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也很喜欢举这个例子,在美国,每年有巨额资金投入到缩小班级规模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知道,班级规模缩小需要增加师资、教室、硬件,所以联邦政府州政府把大量的钱投在里面,但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会改进学生的成绩呢?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一个有选择的社会里面,如果要是有一个班是小班,一个班是大班,大家马上就想到,谁会去选择读小班?往往就是富人,因为他有钱,还有就是父母的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也会觉得小班好,所以就会让孩子去读小班,于是就会看到小班的成绩好。但是小班的成绩好是不是因为父母有钱呢?是不是因为父母的学习成绩就比较好呢?还是因为班级规模缩小导致的呢?所以凭我们的肉眼观察到的,小班的同学成绩好,这不说明任何问题。如果这个政策没有效果,你要知道,给政府节省下来的钱,不知道可以造多少航空母舰了。那么在这样的研究里面,政策评估所起到的对于人类福利的改进,对于社会价值的创造就远远大于一个单纯的理论研究。
所以,为什么应用的研究和政策的评估如此之重要?很多人觉得文科好像没什么用,文科就是大家拍拍脑袋,想想 idea 就可以了。现在的实证研究已经可以为增进社会福利,提高资源的有效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反过来看中国,我一直讲的一句话就是,有政策无评估,我们做了大量的政策,我们有没有评估?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些政策有没有效果?我们不知道。
在经济学最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有一场新的热潮出现在三个领域,我也一直在讲,一个是比较经济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新的政治经济学,还有就是社会经济学。我这里特别要强调比较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新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就是要去看各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绩效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本身就带有比较的视角,那么这就马上带来一个问题,是不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对经济的绩效和增长有不同的影响?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实证问题。因为在理论发展之前,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事实,如果它不能被确认,那就不要去做理论了,就无所谓我们讲的 comparative economics 或者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了。
大家现在学经济学理论,学微观宏观理论的时候,你们会在你们的教科书上看到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名字,于是大家就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这些代表了经济学的前沿方向,代表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们在微观宏观里面,特别是在公共课里面的微观宏观,而不是专业的微观宏观 seminar 或 workshop 里面所学到的,都至少是二十年前的东西。因为诺贝尔奖通常都授予二三十年前的成果。你们更应该关注克拉克奖,去看看克拉克奖得主最近在做什么东西,看看那些在世界经济学界处在最前沿位臵的人在做什么东西。我列举几个名字给大家听听,这些人我不能说他们是做实证研究的,但是我必须要说他们大多是既做理论也做实证的,而最近的工作很多集中在实证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人呢?Murphy, 现在在 Chicago, Becker 的学生。Levitt,前几届克拉克奖的得主,他很有趣,他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个笑话,他上课上到微观经济学的时候,问他的同学什么叫全导数?他的同学看着他说,你死定了。可是就这样一个人最后得到克拉克奖。他的工作完全是实证,待会儿我会举到他的例子,比如他会去看堕胎和犯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还有政治商业周期在实证上是否可以证实?再接下来的两个人现在都大名鼎鼎了,我估计未来也可能是诺贝尔奖得主。Shleifer 和 Acemoglu,这两个人一个在哈佛,一个在 MIT,而且这两个人都是研究理论出身的,Shleifer 以前做 corporate finance 的,Acemoglu 主要做 labor economics 的,尤其是 human capital, 最近这几个人大量的工作在做实证,而且这两年他们最著名的一项实证研究,也是引起这两个人争论的一个研究,就是 institution and growth,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人还没有得到克拉克奖,但是我觉得他完全够格,他也是 Becker 的学生,Edward Glaeser,这人也在哈佛,他也做理论,但他最近大量的工作也在做实证,比如 social economics, 还有就是在 institution and growth 方面他也做过,这人什么都做,d 城市经济学里也执一方牛耳。你们看看这些人的研究工作就知道国际的前沿在什么地方。
二、实证和理论有怎么样的关系?
我今天站在这里讲实证的课,我会跟大家鼓吹实证有多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不重要。有一次上课,有一个同学听见我讲了这句话以后就问,陆老师,你实证重要,到底理论重要还是实证重要?我说,现在还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如果有个人告诉你,理论比实证重要,你就把他当疯子就可以了。理论和实证都重要,我今天讲实证重要,并不意味着理论就不重要了,相反,理论非常重要。那么理论和实证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先讲两句话给大家听听,这话都不是我的话,是别人说的,我来转述一下。
第一个是我的同学,现在在加拿大女王大学,丁维莉。她有一次讲到一句话,她说我为什么把实证研究来作为我职业的选择呢?因为有一次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有两个搞理论的人争得不可开交,后来有一个实证经济学家说你们别吵了,我给你们看看证据,于是理论经济学家就不吵了。她说从那以后她就坚定了自己做实证经济学的信心。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讲到的我的一个学生,现在在鲁汶大学,叫纪月梅。这次寒假的时候,我也跟她讲,面对很多来自于学生的困惑,就是学生不重视实证,觉得实证很简单,很好做,理论做不了再做实证。她现在做理论,但她在听我讲这句话时眼睛充满了惶惑,她心想复旦的学生怎么会这样,然后她就讲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实证经济学家应该多看理论文章,而理论经济学家应该多看实证文章”。为什么呢?大家想想看,什么叫经济学?我借用王永钦老师的一句话说,经济学理论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发现。经济学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本事,说我们来创造一个理论?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的本事在于发现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规律是什么?那么什么是规律呢?规律无非就是去解释,x 为什么会导致 y?那么在这之前,你首先要知道 x 导致了 y,于是你才去解释为什么 x 导致了 y。所以实证经济学对于理论来讲,就可以帮你提炼出在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事实。就在这个礼拜二,在图卢兹读博士的李婷到我们学院来做 seminar,她是做理论的,她说,“我这次回来,觉得在中国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我每天看报纸看新闻,我就跟我妈讲,好多事情都可以做一篇文章。”她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理论经济学家的灵感是来自于对现实的观察。报纸是一种观察,电视也是一种观察。而实证经济学家可以做的是提供一种更加科学的,可以被大家确信的观察,如此而已。计量经济学家基于大样本的数据和科学的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更加可信,如此而已,所以他可以给理论经济学家提供事实基础。
我刚才讲了实证对于理论为什么重要,那接下来要讲的是实证也必须要基于理论。这里我就要反驳大家一种观点:你们看大量的计量文章的时候,看到的是计量经济学家把 10 几个变量往方程右边一摆,就出结果了,反正 stata 都会自动报,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说 x 和 y 正相关,x 和 y 负相关,就 ok 了,不是这样的。
实证研究必须基于理论;第二个方面,就是避免 datamining;第三,──可能这话稍微有点过分,──对于理论经济;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就是,数理的模型和计量之间的关系;第一,理论已经有了,可以直接去检验,这个时候你的;第二,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互相竞争的理论,我们就去检;第三,如果机制已经非常清楚,并不需要什么东西都写;第二个例子,大家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有所谓居住区的实证研究必须基于理论。当然我这里讲的基于理论并不一定是指基于那些已经发表的数学模型的理论,不是这个意思。你在做实证研究的时候,一开始,从变量的选取到变量的度量,再到模型的设臵,都必须要基于理论,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必须要有理论基础,要能说出为什么,否则你要提高计量方程的 R 2 非常容易,就一次项放了放二次项,二次项放了放三次项,三次项放了放四次项,……可是有什么意义?如果这样去做计量,没有意义。在放每一个高次项的时候,为什么变量间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根本不知道,因为现在的经济学理论如果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有一个非线性的关系,通常在二次项的时候就停止了,很少有人告诉你还有三次项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就是避免 data mining。你们以后在作实证的时候会发现,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结果出来以后发现跟事前预期不对,有的时候是不显著,有的时候是你以为是正的,结果出来是负的。有一种做法称之为 data mining,就是试,不断的试,不断的加变量减变量,不断的增加二次项三次项,或者减掉二次项三次项,再加个 log 项,然后再加个交互项,然后把数据的度量从 FDI 变成 trade,……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做计量的人都知道,计量可以帮你得到你想得到的任何结果,这就是 data mining。如果计量都这么做,那太可怕了,那我们就不要去做计量了,事先就已经知道结论了。那么怎么来避免 data mining 呢?在具体做计量之前,你已经有一个理论的判断,然后再去做一个计量,一时发现得到的结果跟理论判断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你首先要去想为什么?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之后再把问题找到,根据你找到的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再去调整你的模型和数据,这就不是 data mining。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data mining 和我讲的根据理论判断去调整数据和模型之间的界限是很模糊的,但只有严格按照理论的指引得到的结果才是经得起检验的。在现在的学术制度下,你如果只是凑结果,而犯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是不可能发表成果。
第三,──可能这话稍微有点过分,──对于理论经济学家,你可以片面而深刻,但对于实证经济学家来讲,必须全面,而且悉心洞察现实。大家知道做理论, x 和 y 之间的关系或者相关性,有很多种可能。对于做理论的人来讲,其实他们的工作就是讲一种可能的机制就行了。如果你希望自己的模型复杂一点,丰富一点,可以多讲几种机制,但不需要把 x 和 y 之间所有的机制在一个模型里全讲清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理论经济学家可以片面的深刻,但做计量经济学就不能这样了,因为当你遗漏掉一个重要的机制或者重要的变量的时候,首先就会出现系数估计的偏误。所以对于计量经济学家来讲,在想到要做一个问题,接下来要去选数据、建模型的时候,必须事先对文献非常熟悉,就是理论经济学大概做过什么,有一些什么理论?前人在做类似的工作的时候怎么设模型,怎么选数据的?之后再做自己的工作。这个时候,遗漏掉任何重要的变量和文献都是非常危险的。
接下来要讲的问题就是,数理的模型和计量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一种看法是说,计量之前要先写一个数学模型,这样才上档次,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计量模型可以建立在数学模型的基础上,我只能说这更好,至少是好于或等于没有数学模型。但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必需的东西,而且我特别要反对的是,大家为了追求计量模型前面要有一个数学模型,就硬摆一个数学模型在那里。我碰到很多文章,前面的数学模型跟后面的计量模型根本对不起来。那么,什么时候数学的工作在计量之前不是必需的呢?我列举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理论已经有了,可以直接去检验,这个时候你的创新就是提供证据。比如说,在理论上,在美国教育经济学界,大家都认为学校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学校的效率,于是会对学生的表现有正面的影响,理论上大家都认为是这样,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你不需要有数学模型的,只需要直接去检验就行了。而且现在在做的这方面的工作都没有数学模型,这也成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
第二,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互相竞争的理论,我们就去检验一下到底哪个理论更重要?比如我刚才讲的,我们自己也做的,不平等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人讲是正的,有人讲是负的,那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到底是正是负。有人讲短期是正的,长期是负的,那我们也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短期和长期是不是有这样的差别。
第三,如果机制已经非常清楚,并不需要什么东西都写成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是帮助我们看人脑可能看不清楚的机制的。如果人脑的思路已经够清楚了,就不需要数学模型了。比如说,在 social economics 或者教育经济学里面有这样一些课题非常热,第一个是 peer effects(同群效应),说的是你的成绩受到你同学的影响。比如在同学中会看到喜欢学术的往往是同一个寝室的,大家相互影响就都喜欢学术了,喜欢打电脑游戏的也住在一起,这就是 peer effects。那么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用一个数学模型去写,为什么喜欢游戏的人会影响到周围的同学呢?对于做实证经济学的人来讲,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存在的,我只不过是去 identify 到底是因为人们住在一起以后才受到了 peer effects,还是相同类型的人事前就选择住在一起。对于实证研究来讲,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例子,大家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有所谓居住区的分割,就是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富人和富人住在一起,然后有人就说,当存在 social interaction 的时候,由于穷人和穷人在一起,大家都相互有负面的影响,富人和富人在一起互相也有负面的影响。于是穷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就减慢了,他们的失业概率就提高了。可是这里面就碰到实证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你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到底真的是因为 social interaction 导致的,还是事先对人力资本都不偏好的穷人选择住在了一起?这也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数学模型呢?对于实证经济学家来讲也可以不写,因为更重要的是去 identify 到底是哪种情况导致的?人和人住在一起就会相互受影响对于实证经济学家来讲不需要去写数学模型。
第三个我要举的例子就是 social multiplier。大家知道在经济学很喜欢乘数,比如凯恩斯乘数,就是一点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凯恩斯乘数放大。现在社会经济学的发展里面就提出这样一个新的概念叫 social multiplier。就是说如果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存在的话,那么一点点政策的效果就可以通过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不断放大。比如上海市有一个项目叫“百万人学礼仪”,就是政府投入一笔钱来让大家提高礼仪修养。大家想,你学了这些礼仪之后回到你的社区或者同事里面,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个人穿得好了或者吃饭的样子好了,他就会来学你。那么这种效应不需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实施就会存在,所以你在去评估整个政策效果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最终效果,这个最终效果除以政策直接作用的那个人的效果就是这个 social multiplier 的大小。在实证上这个 social multiplier 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到底有多大?这个也成为实证研究上非常前沿的课题,这个也不需要数学,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就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就产生了。
在有一些研究课题里面,实际上经济学家已经出现理论经济学家和实证经济学家的分工,就象物理学家已经分工为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比较优势是在实证方面,你不需要去做理论经济学家应该做的那些工作。因为在某些研究领域里面,理论经济学家所用到的那些工具和实证经济学家所用到的工具相互的进入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social network。社会网络的计量有一套方法,但是对于社会网络的形成的数理建模用到的数学工具是图论。我不知道什么是图论,我只知道这个词。在我做的工作里面,我也会去做 social network 的形成和影响。但我要去做 social network 是如何形成的理论工作,对我来讲就是找死了。所以像这样的领域里面,你进入的时候就应该清楚你想做什么样的经济学家,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会用图论的就比那些不会用图论的更加高明和聪明。因为对于那些做理论的人来讲,他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现实里有没有。这时候你要定位自己是一个实证经济学家,你就大胆去做就好了。
三、实证研究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告诉大家,实证研究在很多领域里面它是研究的前沿。那么,实证研究在哪些领域里面构成前沿呢?第一个在劳动经济学里面,实证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劳动经济学是一个典型的学科,它的理论已经基本上趋于完善了。所以,在九十年代以后,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劳动经济学家,基本上大家就会把你理解为是一个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家,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家。这个学科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以实证为主的阶段。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两个例子,在产业组织和人事管理经济学里面,这些学科是从理论开始发展的,但是在它的理论大发展的时候,由于数据的公开性问题和数据的成本问题,经验研究非常少。而现在这些年,经验研究在这些领域里面构成了前沿研究领域。
第三个就是在很多的研究问题里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事实是怎么回事。我们都能体会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制度、文化、人的行为,包括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跟现在经济学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不太一样,我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不太一样,但是从经济学研究来讲,我们实际上缺乏可以被经济学科学研究所确认的差异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到底有多大?我们不知道。所以现在大量的对于中国问题的理解,我们仍然是基于在西方的事实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研究和理解中国的事实,但这样做,在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对中国的问题看不透。如果你要提出一个对于中国的理解,构建一个新的理论的话,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实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因为我可以告诉你,在经验研究上它是有差异的。
我特别想强调实证研究在中国特别重要的几个理由:第一个是我刚讲到的,中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什么地方不一样?事实还不是很清楚。第二是制定政策的需要。在中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养一批经济学家,他们可以不关注现实问题,就在书斋里读书,写 paper,做所谓的纯理论。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对应用研究的需求一定是非常大的,对此,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policy evaluation,基于实证研究的政策评估。大家知道中国政府现在都讲科学决策,什么叫科学决策?在英文里面没有一个词叫 scientific policy making 的,但英文有一个词叫 research-based policy making,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决策的英文翻译,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也就是要多做研究。此外,中国的实证研究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和趋势。以后你们有机会去参加会议,特别是国际会议里面关系到中国问题的会议,你就会发现,经验研究所占的比重是绝大多数。
这就反映了经济学家意识到经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而言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工作。比如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的学生张爽和我的文章被厦门大学一个非常高规格的劳动经济学的会议接受,因为是洪永淼教授组织的,请了很多大牛,包括 Heckman,诺贝尔得主级别的。有人在会上说,我们到了中国来就是希望知道中国在发生什么,可是我们没有听到这个。所以,我们在中国做研究,首先要做的还是踏踏实实地告诉大家,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是发现有差异,那么我们就需要新的理论。
最后,由于前面三点,它就会关系到你的资助(funding)。你要去争取一些项目,包括国际的一些项目,都涉及到 funding 问题。
四、如何完成一项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一样,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讲,往往比较容易关注到中段。就像在吃一条鱼的时候,就看到鱼肚子很肥,但你们不知道在做这项研究之前和之后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而这个之前和之后的工作往往占到 70%的时间,但你们就看到这个中段,就是 paper 本身。那么对于实证研究来讲,之前需要做什么呢?
首先,在你做实证研究之前,你要有一个 great issue(大问题)作为你的研究背景。这就是“大处着眼”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small point,也就是我经常讲的“小处着手”的问题。有了一个 great issue 就使得你的研究重要,而有了 small point 又使得你的研究具有可操作性。之后你要有一个好问题(good question)。比如我刚讲的,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到底重不重要?理论制度经济学家就会告诉你很重要,可是对于实证研究来讲,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当你看到制度好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它经济发展水平高了所以它有好的制度。那么对于实证经济学家来讲就要去看 from institution to growth 的这个因果关系(causality)到底有没有,这就是一个 great issue。那么,small point 是什么呢?在 Acemoglu 做的研究里面,他就想,怎么去把这个 causality 确定下来呢?他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变量,他去看非洲、拉丁美洲等殖民地时期的自然条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死亡率。他的想法是,如果在那个时期这些殖民地的死亡率高的话,白人就不愿意住下来,这样他们就会采取掠夺式的制度。如果愿意住下来,他们就会移植欧洲的好制度。那个时候制度的情况就会影响到今天一些地方制度好坏的差异,于是,这就很可能带来增长的差异。通过这样一个链条的作用就可以确认制定是导致增长的原因。这个做法就是一个 small point 使得他的研究变成了一个可操作的研究。
再接下来我举的一个例子是 tea 和 sex。大家知道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 sex imbalance,女孩子太少,男孩子太多。经济学家的一个解释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讲,生男孩比生女孩好。因为男孩的生产率高,工资高,于是投资一个男孩的回报就更高。这个解释很多人不太喜欢,说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生育行为不对,他们觉得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大家都不喜欢女孩子,歧视女孩子。那么经济学家讲的到底对不对呢?于是就有我刚讲到的 tea 和 sex 研究里面,有一个美籍华人叫 Nancy Qian,她是前年的美国 job market 上的 star,现在到 Brown 去了,她来过复旦两三次。在她的研究里面就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家庭生育行为是一种经济决策。她想到,在改革开放以前,各种商品的价格都是被管制的,改革开放以后价格在逐渐放开,于是经济作物特别是茶叶的价格上涨了。大家知道摘茶叶这件事是女孩子的比较优势,因为女孩子比较细心。那么,根据经济理论的推断,茶叶的价格上升就会导致女孩的回报提高,这样就会使得家庭更加愿意生女孩,就会在孩子出生以后给女孩更多的照顾以减少她的死亡率。于是她就用了这样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价格改革这个自然实验提高了女孩的回报,于是提高了女孩的出生率和存活率,结果她的研究发现就是这样的。
那大家可能马上就想了,这些都太复杂了,我做不了。做不了可以做些简单的,比如我要讲一个矿难的例子,当然这个也不简单,因为你要是研究矿难会很麻烦。但我想举个例子,前年的经济学年会上,有一位老师说,他观察到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提高矿难职工死亡的补偿费以后,矿难反而增加了。为什么呢?根据经济理论,这有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道德风险。如果安全措施是由经济决策决定的,而生命是有价值的话,矿难水平提高了意味着如果减少安全措施,一旦发生事故,补偿金水平提高了,这就会增加人的道德风险,降低安全的保障措施,这就有可能导致死亡率上升。问题在于,你们如果学过信息经济学,要做出一个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的理论是非常容易的。可是这里面就遇到一个问题了,他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补偿提高以后矿难的发生率反而提高了?或者说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文章做出来,一定是非常好的文章,因为它是一个大问题,它可以证明,人的生命是不是可以用价格来算的。
在你提出一个好的问题以后,一定要充分去做文献评论(literature survey),这可以达到几个功能:第一,通过文献评论你可以去证实你的研究为什么重要。比如我刚讲的矿难问题,如果你的文献评论是这样做的:某年某月有个人说,这两者是正相关的,所以我这篇文章就要去证明这个,那这篇文章就没人感兴趣了。如果你的文献评论是这样的:在经济理论里面有人提出,人对于安全设施的投入是一个经济的计算,对此很多社会科学家是有争论的。比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经济学家的这些观点是错的,这篇文章通过矿难的案例来告诉你经济理论是否正确。人家就会觉得非常重要。第二个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要说明 what’s new?我们做研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 what’s new。你做一个东西出来,你的读者为什么要看?你一定要在做的过程中想办法在你的东西里挖出一些新的东西来吸引你的读者,因为看文章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有成本的。我们很多同学以为,我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但我不说,我很酷。我告诉你,如果现在做研究就抱着这样的心态,你死定了。你做一项研究,你一定要竭尽全力地要把你的工作在 idea,method,data 这几个方面跟既有的研究去做比较,来告诉大家,我用了一个不同的 idea,我用了一个不同的方法,我的方法能够得到更加准确或者 unbiased 的估计。我的 data 是新的,别人的样本很小,我的样本大,别人没有这个度量,我有这个度量,所以我新。
再来谈研究之中,这个时候你首先需要一个理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理论和分析框架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需不需要数学?这我刚才已经回答过,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个就是数据(data)。你的 data 哪来呢?当然我们有很多现成的数据,比如象我们做实证研究的,手头都有一些数据,但是你们以后去做实证研究,不管是去公司里做还是在学术界做实证研究,往往你需要自己去收集数据,这个时候你的数据是第一手的,尤其是在初始起步阶段的时候,你的样本不可能太大,样本大就需要钱,你没那么多钱,这样你的样本量不太大。那你要做这个研究,怎么才能让自己的研究成为一个好的研究呢?你就要去考虑。首先,你要新,你要注意,是不是在你样本不大的数据里面有一些变量是别的大样本的数据没有的;第三,你要有非常聪明的 idea,当然这很难了,所;最后是计量分析(econometricanaly;比如在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研究里面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研究之后我们得到很多结果,这时候你还有一些工作要;如果你象刚才讲的那样去做了,我就要祝贺你了,因为;五、一些评论;接下来我再做几个结论性的评论;除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这些机制性的东西以外,案;第二种情况是的。或者你研究这个问题别人从来没研究过,你是第一次通过收集数据的方式来研究。
第二,一定要是 well defined,就是你这个数据一定要非常清楚地定义。比如,根据已有的文献,social capital 是定义为这样几个方面,它们都是这样去度量的,用什么样的问题来问的,所以我在我的问题里面也这样问,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好的度量(good measure)。最后,你的数据要 well structured,就是该有的变量你要有,你想 identify 的那些机制的中间变量你也都有,那么即便你的样本小一点,也可以做很好的研究。
第三,你要有非常聪明的 idea,当然这很难了,所以要求就越来越高了。在计量里面,通常来讲你看到的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只能说它是一个相关性 (correlation),但现在的实证研究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相关性,而是要去看 causality。看因果关系一个常用到的方法就找工具变量。那么,这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看 causality?用 natural experiment?用足够让大家确信的外生变量?还是去找工具变量?这就需要你有非常聪明的想法来让大家确信你看到的确实是一个 causality,而不是一个因果不明的相互关系。当然这个要求比较高了,在很多研究领域里面都是前沿课题。对于我们来讲,有的时候不要随便说你找到 causality 了,就是发现相关就很不容易了。
最后是计量分析(econometric analysis),就是要去分析、回归、解释结果等等。我们得到结果以后就可能碰到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会发现,这个结果好像不对,我们感觉到的现实好像不是这样的,具体表现为符号或者显著性不是事先预期那样的。这个时候就要注意,有可能问题出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你一定要去想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然后再去调整它,而不要去做 data mining 的工作。第一个,数据可能是不好的。数据不好的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用了中国的数据。中国的很多宏观统计指标是很粗糙的,比如中国的失业率本身就不是真实的失业率,你用了就有问题了。还有可能你的样本不是一个随机的样本,还有就是你的样本量太小了,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你的数据质量不高,从而你想看到的东西看不到。第二个可能性就是理论出了问题。这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之前基于的理论是错的,或者它根本不反映现实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可能存在一个新的理论或机制,它抵消了你原来认为的那个机制。
比如在我们自己做的一个研究里面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做经济开放和国内市场分割这个相关性的研究的时候,本来觉得开放了使得竞争加剧,竞争加剧应该使得国内市场整合,结果后来发现往里面一放是线性关系,而且是正的,就是开放是促进市场分割的,那我们就想为什么?有可能是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开放是促进市场分割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开放就促进市场整合了,于是有可能存在二次的关系,我们把二次项往里面一放,果真一个非常漂亮的 U 型曲线就出来了。当你在正确的理论指导的情况下去做计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加东西,是改变模型的形式还是改变数据,还是改变你的 measurement?之后你在理论的指导下得到的结果就可以帮助你发现新的东西,因为在我刚才讲的这个 U 型曲线的下,就告诉我们,在理论上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分割的程度取决于开放的程度,这个是在既有的理论里没有的东西。事实上你们在座各位如果有人对此感兴趣,你就完全可以去做这样一个理论来描述经济开放和市场分割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象我们所看到的 U 型,这时候你就知道理论和实证是一个什么关系了。理论是怎么来的?不是凭脑袋想起来的,是把现在已经发现的事实和规律形式化(formalize)。
研究之后我们得到很多结果,这时候你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第一个就是你要去解释它,我们很多同学做完了计量以后说,我的结论是 x 和 y 正相关,x 和 z 负相关。这毫无意义,就象你做了一个数学模型,做出来以后,它的经济学含义是什么?你要去解释为什么是正的?为什么是负的?为什么有非线性的关系?另外大家要区分两个 significance。一个是 econometric significance,它指的是在统计上 x 和 y 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显著的。还有一个是 economic significance,它指的是系数到底有多大,就是经济上的显著性,它能告诉你一个因素的重要程度到底有多高。然后你还要在这个基础上得到 policy implication,即政策含义。
如果你象刚才讲的那样去做了,我就要祝贺你了,因为你已经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向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前进了。
五、一些评论
接下来我再做几个结论性的评论。第一,尽管我前面讲了计量如此之重要,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个评论是,large sample plus econometrics is not everything。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做计量、做实证,唯一的路子就是去做大样本加上回归。首先,计量经济学所做的很多工作,往往还不足以 identify 两个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在这个层次上,计量和理论是互补的。理论能够帮你解释,为什么 x 和 y 是正相关的?机制是什么?而实证帮你看到的只是 x 和 y 正相关,如此而已。
除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思考这些机制性的东西以外,案例 case 有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济学家现在已经非常看不起 case,但是我觉得 case 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机制在计量里面是不清楚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做一些 case study,去观察一些现实来告诉你,你为什么在计量上有可能看到 x 和 y 是相关的。
第二种情况是,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不能度量的。计量经济学一个依赖的前提就是每一个东西都可以度量,但是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度量呢?比如什么叫制度?什么叫法律?什么叫产权?什么叫民主?其实,有的时候,一些可度量的东西往往没有不一定能准确地捕捉到现实生活中的机制。
第三,有的时候数据几乎是不可得的,但是问题非常重要。比如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在经济学院作过一个报告,讨论中国的私有化和腐败。通过案例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在中国,私有化导致了腐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以前就设臵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制度结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如果你想用计量经济学家来告诉大家私有化造成了腐败,你要有 large scale sample。比如你要有 500 家企业,而且你要找到腐败的度量,你能通过问卷得到腐败的大小吗?所以这种情况下案例就非常重要了。讲到这里,我就特别要强调,计量有计量的好处,它是大样本的,比较可信。这时候你在那些可以度量的、可以收集数据的问题上,就尽量要用计量的方法。案例用在数据几乎不可得、问题和作用机制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你千万不要去做那些大家都觉得可以用计量来做的,你说你用案例来做,就没有人信你了,因为案例可能就只有几个观察点。
2004 年的时候我发表过一篇文章《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有几句话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第一,计量是有陷阱的。我刚才讲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底限,每个人报告什么取决于他自己。由于现在学术的规范,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在国外,你如果发表一篇实证的文章,你的数据就需要公开,要使得你的审稿人可以重复,这个时候你就不敢随便报告结果了。
第二,你会发现在实证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经常是有一篇实证文章说前面的结果不可信,我得到的是可信的,而结果是相反的。那大家就很慌,为什么呢?因为做理论,你只要证明 x 和 y 是正相关,它确实在纸上是对的。但做实证,已经发现 x 和 y 是正相关,但你却明明发现它们是不相关的,那你就很慌,就生怕过了三年自己的文章没人引用了。可是我觉得这里面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计量到底是什么?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特别是计量工具就像我们在研究天文现象时候的望远镜,望远镜可看的远的程度相当于计量方法的科学性的程度。
计量的方法是在不断地往前推进,随着方法的推进,以前得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不可信的了。这就好比你用望远镜去看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你没看到上帝,你就以为上帝不存在了?不一定的。只是现在的望远镜看不到。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最后实际上是无穷逼近于神学的。所以我们千万不用怕,觉得我们用的方法不够先进,没有看到正确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说,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所有的研究都是错的。因为如果没有当初的地心说,我们到现在还以为世界就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恰恰是因为有了地心说,后来才慢慢有了日心说。
再接下来看一张漫画。它讲的是非典型性肺炎的意思,很多盲人去摸这个象,有人说是恐怖袭击,有人说是病毒,有人说是细菌,就好像不同的计量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我们到底应该信谁呢?Feldstein 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故事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每个盲人带着片面的、“不正确的”印象而去,而在于聪明的王公(经济学家)研究了这五个盲人的发现后,能把各部分拼在一起,形成对大象的正确判断,特别是如果他以前曾看到过其他四腿动物的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我们对于世界的准确认识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并不是说你要去相信某一篇文章,你如果想形成对这个世界的整体看法,你是把很多实证文章放在一起,每一篇文章可能都是盲人摸象,但对于你自己来讲,对于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来讲,应该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形成对这个世界相对来讲比较完整的看法。
比如我刚才讲的不平等和增长的关系,大多数人的研究都认为它们是负相关的,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相信两者的关系确实是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反复做的原因。有的改进方法,有的改进数据,因为在不断做的过程当中,不断重复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对变量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讲到这里就差不多该结束了,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走向现实,让我们将实证研究进行到底。